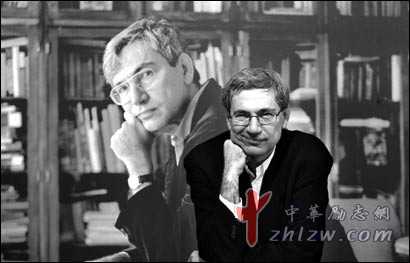
“土耳其是个毫不吝啬任何机会去对国内帕夏(旧土耳其高官尊称)、圣人及警察歌功颂德的国家;作家冀盼同等待遇?非先要忍受法庭和牢狱的折腾不可。难怪去年朋友们知悉我惹上官非,无不带笑褒奖:你总算是个真正的土耳其作家。”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、54岁的土耳其作家奥罕.帕穆克(Orhan Pamuk)接受杂志《纽约人》访问时说。
得奖消息公布后,土耳其外交部发表声明,恭贺并赞扬帕穆克,同时表示,人民早已期待能有“土”产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诞生。
大胆言论惹来国家震怒;遭反对人士焚烧其着作及相片泄愤;收到死亡恐吓逃命;起诉罪名若成立,可能要受3年牢狱之苦……
总算安稳度过,帕穆克说:“最好尽快回归作家的生活、写作、出版。”
帕穆克在伊斯坦布尔的住所。从阁楼眺望,举目华丽的历史、文化痕迹:圣苏菲亚大教堂、马尔马拉海、博斯普鲁斯海峡……这是环抱他创作的背景,引发他写作的养份。“自小,我认为世界不局限于个人的体会:在伊斯坦布尔某街角、某所与我家相似的房子里,存在着另一个我,体验另一种人生。”
分裂 消化 融合
他接受英国《卫报》记者访问时表示,儿时每当父母吵架令他不胜负荷,想要逃避,总爱跑到妈妈的梳妆台前,调节起那眼前的三面镜子,直至镜中自己的倒影不断重叠化身无穷,消化掉存在于现实的自己。
“我叫这做『消失的游戏』,而这『游戏』的形式,日后常见于我的作品中—万千的自我,化身声音、零碎,无形地成为故事与情节的叙述者。”他说。
零碎与多重叙述者,成为了他的风格。基于这概念,帕穆克创作了震撼国际文坛的《白色城堡》(The White Castle)故事:内容描述一个被奥斯曼海盗俘虏的威尼斯人,卖给一个跟他长得一模一样苏丹宫廷的官员;此后,他们交换两个不同文化的知识与生命经历。自己遇上自己,好精神分析的概念。
土耳其人 一体两魂
“我认为《白》的故事,呈现很严重的自我挣扎,同时是一个有关双重身份的故事。”帕穆克表示,凭该作品真正冲出国际之余,亦突然有所顿悟。“我把《白》的意念构建在国际层面之上,忽然发觉双重身份,其实是土耳其民族的『特色』,差不多有九成土耳其人是『一体两魂』的。”
帕穆克强调,国际间指出土耳其人在思想上划分为“好人”(非宗教派、民主派、自由派)及“坏人”(民族主意派、反国家集权派、保守派)两类;然而现实之中,普遍土耳其人的思想意识上倾向“好”“坏”并存。某程度上不断自我挣扎,甚至活在自我矛盾的阴影下。
“相信当土耳其力图加入欧盟时,国内一些极右民族运动分子,在当地默默起动某些民族主义运动。他们不断刺激着土耳其人民面对西方文化的不安情绪,还替国家捏造出一个虚构的『过去』,企图令国际间相信,土耳其被西方文化力量所蚕害。”
他认为由这些行动,引发出的民族伪装感,间接促使他受到国际间及国内人民的抨击。
影子与实体的重叠、自我与自我之间的混淆,帕穆克于2003年推出悬疑推理式故事《我的名字叫红》(My Name Is Red)。
内容讲述,16世纪的伊斯坦布尔,苏丹请来一些伊斯兰艺术家创作一本欧洲风格的书;众人在接触各种来自西方的风格、原创性及表现手法时,感受到的诱惑及矛盾。
故事的结局是血腥的(谋杀)、终极的(死亡),并清楚揭示人类的文明,难免受到陌生且垄断性的强大文化所占据侵蚀。
对伪现实与憎恨的悟
“土耳其人受到传统奥斯曼文化、伊斯兰文化、西方文化的冲击洗礼,衍生出对西方甚至尘世的某种脆弱情感,包括:伪装感、缺乏感、对国家的恨等,是相当可耻的反应。我认为世上某些国家,不少民众仍然面对着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局。要理解世界或其他地方的民族主义,及反西方情绪的根源,必然要更深入了解这些国家的种种问题。光着眼于某某国的政治进程,只是流于表面观察。”
他被问到,有否认为自己是土耳其“自我憎恨”情绪下的受害者:“没问题,谁都有些『自我憎恨』吧。反而,若不能够走出这胡同,或处理不当的话,后果严重得多。所以,能够去确切认知『自我憎恨』的知性功能,某程度上,可帮助一个人去了解其他人的思想和行为。”
所谓快乐……
去年,帕穆克的爆炸性言论—他指土耳其不敢面对曾屠杀库尔德族少数族裔及亚美尼亚人的事实,引来当局的抨击和刑事起诉;他被指对土耳其伊斯兰文化作出批判,受到回教徒反击……
如此人生,何来快乐?
“若抛开感官的满足、*爱的满足、丰衣足食的满足、睡得好的满足……对我来说,能够写作出两、三页好文章,大概也乐透了。”帕穆克说。
也许帕穆克的素愿,如他旧作《新人生》(The New Life)的首句:“某天,我读了一本书,我的一生从此转变。”他盼望着某些转变。
帕穆克的人生,从现在起,顺流逆流,继续旅程。
天天励志正能量